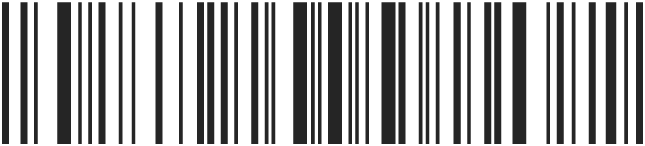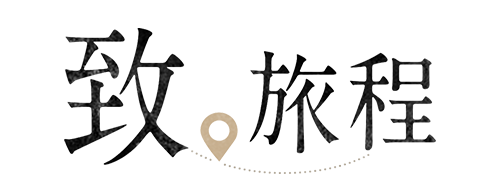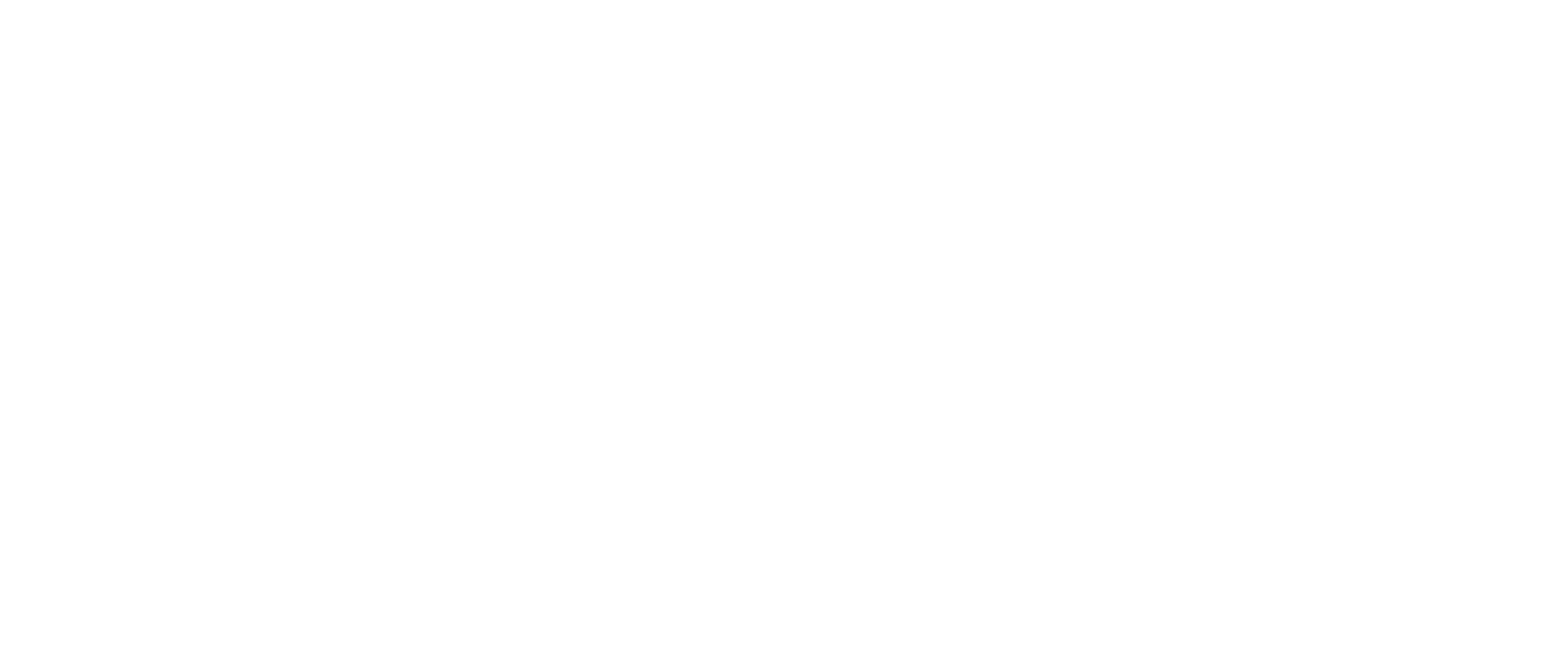白色死神與地圖上的針:那場未曾結束的冬季戰爭與芬蘭魂的底氣
發佈 2026.01.25 |更新 2026.01.28
1939年,蘇聯紅軍踩過邊境,一個地理系學生放下繪圖筆,拿起了步槍。他從不稱自己為狙擊手,而是「邊境校對師」。八十年後,當戰火再次逼近歐洲,他的後代在赫爾辛基廣場上,做出了同樣的回答。這是一篇關於「絕不退讓」如何刻入基因的深度紀實。
• 同一場戰爭,哥哥在雪林伏擊,妹妹在野地帳篷醫院。一顆子彈殼、一片雲莓,串起兄妹各自的戰場。當國家被迫站在生死邊界,戰爭如何進入個人的身體、記憶與下一代?本篇為《芬蘭:生存計算》系列之一。
1939年12月一個濃霧瀰漫的清晨,22歲的芬蘭野戰護士「艾爾莎·科伊武寧」在帳篷裡,為一名腹部中彈的士兵完成了手術。
這是蘇聯紅軍越境進攻後的第三週。
就在一個月前,她還在赫爾辛基的報紙上讀到,史達林要求芬蘭割讓卡累利阿地峽以「保衛列寧格勒」,被祖國拒絕了。隨後,在11月30日,百萬紅軍的砲火便撕裂了邊境線。
她所在的移動醫院已後撤了兩次,面前這條用冰與木樁匆忙加固的「曼納海姆防線」,是首都最後的屏障之一。
她將染血的紗布投入沸水鍋,消毒後需重複使用,補給越來越少。蒸汽短暫溫暖了她凍僵的臉。
緣起:一封沒有字的家書
這時,一名通訊兵彎著腰鑽進帳篷,遞給她一個小鐵盒:「你哥哥埃斯科的部隊在伊諾附近,」他含糊地指了個方向,「這是他託人帶給妳的。」
鐵盒裡沒有信,只有一顆閃亮的7.62×54mmR步槍彈殼,彈殼底部平整地嵌著一片壓乾的雲莓—一種只在最荒僻的北極沼澤生長的橘紅色漿果。
艾爾莎攥緊彈殼,她知道這意味著兩件事:哥哥還活著;以及,他正潛伏在敵人無法想像的、如同雲莓生長地般嚴酷的地帶。
哥哥:雪原上的「邊境校對師」
她的哥哥,埃斯科·科伊武寧,曾是赫爾辛基大學的地理系學生,擅長用等高線描繪國土。
戰爭爆發後,他放下了繪圖筆,領到一支莫辛-納甘步槍,成為遊蕩在拉普蘭雪林中的「白色死神」之一。

莫辛-納甘步槍 圖/wikimedia
從繪圖筆到狙擊鏡
他從不稱自己為狙擊手,而說自己是「邊境校對師」—用子彈修正那些破壞芬蘭地圖、不請自來的腳步。
他憑藉對每一處丘陵與沼澤的熟悉,在零下三十度的極寒中無盡地拖延、騷擾這支龐大的軍隊。
他在地圖邊緣寫下小小的數字,記錄每一次校對的日期。 他知道,他們是在用生命為單位,為談判桌爭取時間,儘管沒人知道終點在何時。

白色死神 席摩·海赫共狙擊542人,讓紅軍聞風喪膽 圖/wikimedia
妹妹:消毒水中的戰爭代價
血紗布與異國母親的呼喚
艾爾莎在後方處理的,正是這種「校對」的代價。她學會了在柴油燈下憑觸覺尋找深嵌的彈片,學會了用最少的嗎啡讓傷兵熬過運送路途。
她護理的傷員中,有一個不到二十歲的敵軍蘇聯士兵,在昏迷中不斷用俄語呼喊「媽媽」。
艾爾莎為他更換繃帶時,動作可不溫柔。
她想起哥哥子彈盒裡的雲莓,想起地理課上老師說,芬蘭1/3的國土在北極圈內,這片土地從未真正屬於過任何人,只屬於能與它共存的人。
如今,整個國家都在為這個「共存的權利」支付代價:用一具具凍成青紫色的軀體,去換取蘇聯紅軍推進表上每一公里、每一天的滯留。
這場後來被稱為「冬季戰爭」的衝突,對他們而言,只是第一個冬天,也可能是最後一個。

生長於拉普蘭地區的漿果-雲莓 圖/wikimedia
終局:割讓的家園與沉默的地圖
戰爭在持續了約105天後,以一紙和平協議戛然而止。
芬蘭保住了獨立,但付出的代價是超過2.3萬名軍人陣亡,祖國永久割讓了11%的國土,包括那片埃斯科曾用雲莓標記過的、名為卡累利阿的家園。
1940年3月和平生效的那天,妹妹在赫爾辛基火車站等到了哥哥。他揹著步槍,臉龐被凍傷和疲憊侵蝕得近乎陌生,唯有眼神依舊銳利如準星。兄妹相顧無言。
105天後的傷痕
最後,哥哥從懷中掏出一張皺巴巴的軍用地圖,在兄妹倆腳下鋪開。一條粗暴的紅線,將他曾守衛的山林與湖泊劃了出去。
「他們拿走了卡累利阿,」哥哥沙啞的說道,「但他們拿不走我腦海裡的每一條等高線,拿不走我們在這裡戰鬥過的事實。」
艾爾莎看著哥哥。她知道,有些戰爭從未在簽字的那一刻結束。它們變成了地圖上無聲的傷疤,變成了此後八十餘年裡,芬蘭人面對東方時,一道不需要說出口的傷疤。
當「西蘇」精神需要一個新的座標
2022年春天,赫爾辛基的議會廣場聚集前所未有的人民。
在要求加入北約的人群裡,有白髮蒼蒼的老兵後代,也有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。風中聽不到演講,只有一片壓低的、堅定的交談聲,像極了祖輩口中,1940年那個簽訂和約後沉默的冬天。

赫爾辛基議會廣場 圖/Shutterstock
2022年,赫爾辛基的冷風與抉擇
艾爾莎的孫女莉娜站在其中。她手中沒有標語,只是輕輕握著手機,屏幕上是她剛翻譯完的一篇戰創傷護理指南—從烏克蘭語譯成芬蘭語。
廣場上的風吹過,莉娜打了個冷顫。一個念頭毫無修飾地擊中她:
「八十多年過去,我們居然還在面對同樣的處境?」
問題很簡單:「當你的生存被當作一個籌碼時,你除了讓自己變得不可被征服,還有別的選擇嗎?」
祖輩的答案是在雪地裡開槍,他們這一代的答案是在這裡站著。
回答的形式天差地別,可裡面那份「絕不退讓」的硬核,絲毫未變。
她忽然理解了那種一脈相承的疲憊,也理解了那種更深層的驕傲。
她收起手機,向更靠前的位置挪了兩步。
這一步,是她的答案。
如何體驗「西蘇」?
文中虛構人物的韌性,源於真實的民族性格。你可以在當代芬蘭這樣觸摸它:
- 在靜默中行走:前往「努克西奧國家公園」,租一雙雪鞋,獨自完成標記清晰的森林小徑。極寒中的寂靜,是理解芬蘭人內向堅毅的最佳課堂。
- 上一堂全民防衛課:赫爾辛基的「國防體驗中心」向遊客開放模擬演練。試著在虛擬的危機情境中做出抉擇,感受「每個人都關乎國家安全」的公民責任。
- 傾聽沉默的一代:在坦佩雷老工人社區的樸素咖啡館坐下。無需多問,只需在適當時機對身旁長者點頭致意,一個關於戰爭、失去與生存的故事碎片,或許會悄然開啟。
這些選擇,並非孤立發生。
下一篇,走進那條注定失守、卻仍然成功的防線。
►《芬蘭如何用「遲滯防禦」,在冬季戰爭中逼退蘇聯?》

芬蘭努克西奧國家公園 圖/Shutterstock
編輯註
本文背景設定於1939–1940年的「蘇芬冬季戰爭」,其歷史脈絡、戰爭起因、戰事時程(約105天)、以及《莫斯科和平條約》所造成的領土割讓與人口遷移,皆依據主流戰史研究與芬蘭官方史料。
文中所提及的作戰環境與元素,包括極地低溫、森林與湖泊地形、芬蘭軍隊的滑雪機動、狙擊手戰術、「白色死神」稱呼、莫辛–納甘步槍、以及女性於後方醫療與支援體系中的角色,均可在芬蘭戰爭檔案館、老兵回憶錄與相關社會史研究中找到對應紀錄。
故事中的兄妹角色「埃斯科」與「艾爾莎」為敘事所需而設定的複合人物,其經歷與細節,融合了多位前線士兵、狙擊手、戰地護士與當時知識分子參戰者的真實經驗。文中出現的具體場景、對話與心理狀態,皆建立在對當時物質條件、醫療限制、戰爭節奏與家庭結構的史料理解之上,並進行必要的敘事重建。
本篇並非意圖完整重述戰爭史,而是嘗試透過個人視角,呈現冬季戰爭如何進入芬蘭人的日常記憶,並影響其後數十年面對安全與生存議題時的集體判斷。
FAQ
Q1:冬季戰爭中的「白色死神」是真的嗎?芬蘭軍隊如何以小博大?
「白色死神」是蘇聯紅軍對芬蘭狙擊手的恐懼稱呼。最著名的代表是席摩·海赫(Simo Häyhä),他在不到一百天的戰爭中擊斃了超過500名敵軍。芬蘭軍隊之所以能以小博大,靠的是「莫蒂戰術(Motti)」—利用極地森林地形將綿長的蘇聯車隊切斷、包圍、蠶食。此外,芬蘭戰士具備極高的滑雪機動力,他們像雪原上的幽靈,讓物資匱乏、不擅寒地作戰的紅軍防不勝防。
Q2:芬蘭的「西蘇(Sisu)」精神,具體代表什麼?
「Sisu」是芬蘭語中難以精準翻譯的詞彙。它融合了勇氣、韌性、頑強與一種「在絕境中依然行動」的硬核性格。它不代表樂觀,而是一種「即便知道成功的機會渺茫,依然要完成該做之事」的使命感。這正是芬蘭能在1939年頂住蘇聯百萬大軍壓境,並在戰後廢墟中迅速崛起的民族靈魂。
Q3:為什麼芬蘭被迫割讓11%的領土仍被視為某種程度的「勝利」?
在1939年的國際戰略預測中,芬蘭本應在數週內被全面佔領並納入蘇聯版圖(如同當時的波羅的海三國)。雖然芬蘭最終失去了富饒的卡累利阿(Karelia)地區,並導致 40多萬芬蘭人被迫遷徙,但他們保住了國家主權與民主制度,沒有淪為附庸國。這種「慘勝」,讓芬蘭在冷戰期間獲得了特殊的生存空間。
Q4:冬季戰爭如何影響2022年芬蘭加入北約的決定?
芬蘭人的集體記憶中深植著一種「鄰居隨時可能過界」的警覺。八十多年來,芬蘭始終維持強大的徵兵制與民防體系,就是在為「下一個冬季」做準備。2022年俄烏戰爭的爆發,讓原本維持中立的芬蘭人意識到,僅靠自身的「Sisu」與外交斡旋已不足以應對當代的安全威脅,因此選擇加入集體防禦體系。這不是背棄傳統,而是傳統生存意志在當代的形式轉化。
芬蘭專題策展|一個小國的生存計算
這組文章,試圖回答一個簡單卻殘酷的問題:當你與一個不可預測的強權為鄰,生存意味著什麼?
策展動線如下:
► 策展入口
與巨人為鄰80年:小國芬蘭,如何將恐懼轉化為一整套生存系統?
► 宏大場景篇
芬蘭冬季戰爭:小國如何阻擋蘇聯百萬紅軍?
>>理解一切恐懼的起點
► 關鍵地標篇
曼納海姆防線:一條注定被突破,卻改寫結局的防線
>>理解記憶如何變成戰略
► 當代迴響篇
2022 年,芬蘭為何選擇加入北約?
>>看見歷史如何在今天做出決定
🔎 你可以從任何一篇進入,但只有走完整組,才能真正理解芬蘭。
| 本文未經同意,禁止轉載 |
主視覺圖 wikimedi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