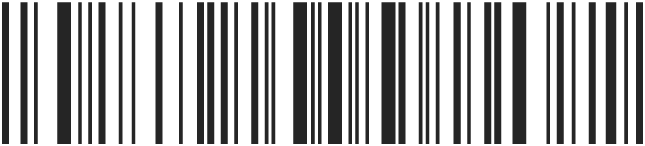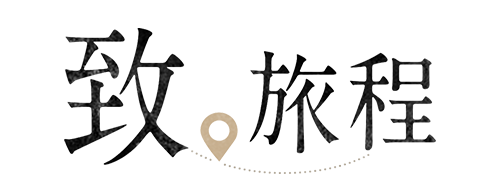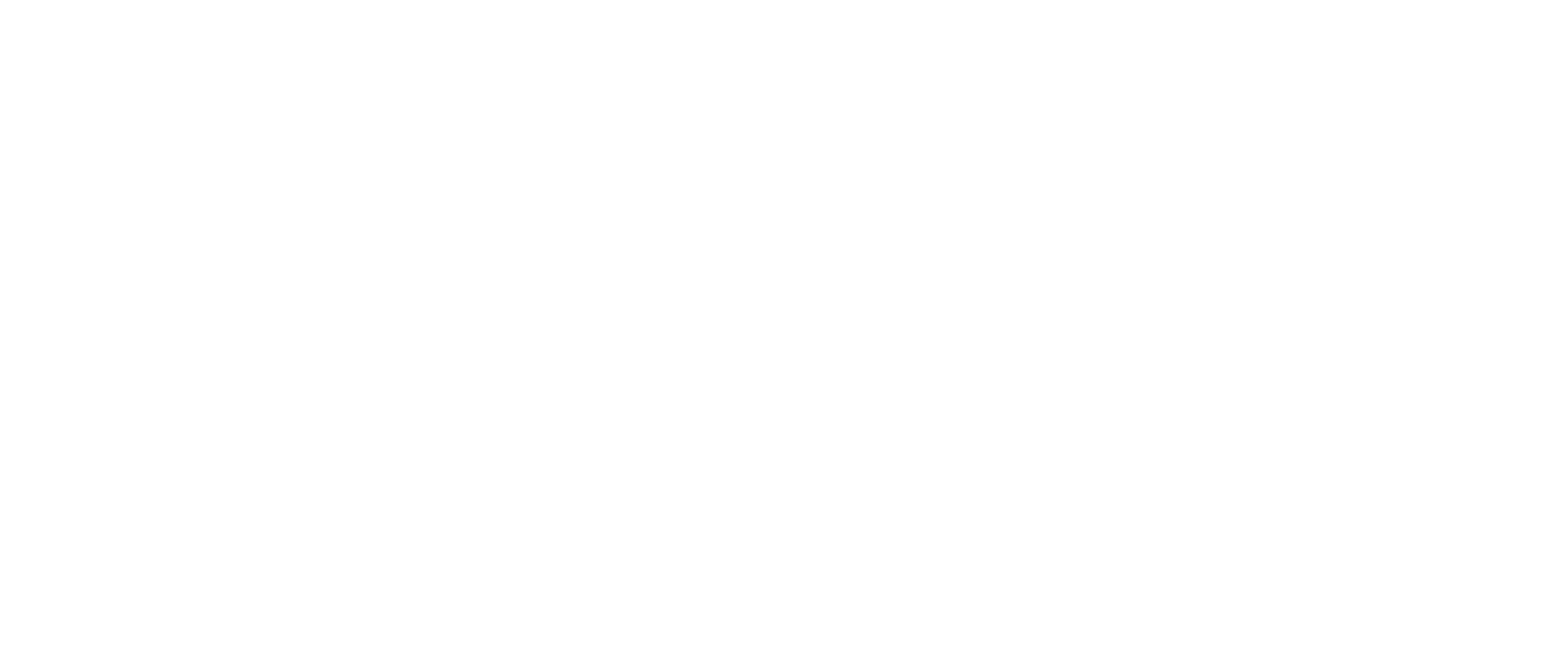愛丁堡歷史如何轉化?從瘟疫恐懼到紀律之城的心理重建
發佈 2025.12.25 |更新 2026.01.08
愛丁堡曾是歐洲最擁擠、最讓人恐懼的城市之一。瘟疫、巫術審判與死亡曾主宰日常生活,但18世紀後,它卻一步步變成以紀律與秩序聞名的城市。這篇文章從人心、制度與時代變化出發,帶你看懂愛丁堡如何從混亂中撐住自己,也理解軍樂節為何會在這裡誕生。
- 一座如末日般混亂的城市,怎麼會變得如此守秩序?
- 愛丁堡的紀律,是一次次被現實逼出來的選擇。
- 當恐懼開始失效,人們還能靠什麼讓城市不要崩掉?
- 20世紀的軍樂節為什麼象徵愛丁堡的治理方式?
- 讀愛丁堡,就是在讀人類如何走出混亂的過程。
在這座城市,秩序是為了生存
站在「愛丁堡古堡Edinburgh Castle」下方,你會很難把「紀律」與「浪漫」聯想在一起。
那座城堡像一塊的黑色岩石,霸道的壓在城市的咽喉上,既不親切,也不帶善意。
但如果你理解愛丁堡的進化過程,你會明白,
這座城市的整齊與優雅,其實是從地獄邊緣撿回來的,她一共歷經了三層轉換:
一、人心的變化:當恐懼治理失效
在16–17世紀,愛丁堡沒有現在的優雅,而是歐洲最窒息的囚籠。
因為被城牆困住,舊城(Old Town)只能被迫向上發展,形成了被稱為「世界第一批摩天大樓」的獨特景觀,最高達14層樓的建築遮天蔽日。
那也是一個充滿氣味的時代:居民從窗戶潑灑穢物,喊著一聲「Gardyloo!」(注意水來了)便讓惡臭滿街;那更是一個驚懼的時代,瘟疫隨時敲門,巫術審判的火堆在街角燃燒。
恐懼,曾是這座城市唯一的治理手段。
當人們害怕上帝、害怕病魔、害怕鄰居,統治者就不需要理性。
但是,當恐懼來到最高點,會讓人疲乏。
死亡變成日常,社會便不再穩定,人民共同積壓的絕望,有一天將成為這座城市的審判日。
愛丁堡終於意識到:必須讓人心學會「自我約束」,秩序才不會徹底崩塌。

舊城皇家哩路 圖 Gimas/Shutterstock
二、城市的選擇:她在混亂中選擇了理性
18世紀,一場優雅的叛逆發生了。
愛丁堡決定不再靠詛咒維持秩序,而是押注在「理性」上。
這就是著名的「蘇格蘭啟蒙運動」。
想像一下,在愛丁堡狹窄昏暗的小酒館裡,大思想家們在濃烈的威士忌與壁爐煙霧中辯論,迸發出超越時代的智慧,這使得愛丁堡當時被譽為「北方雅典」(Athens of the North)。
愛丁堡思想大師
大衛·休謨(David Hume)
人做選擇,多半不是靠理性,而是靠習慣與情緒;連「因果關係」,也只是我們看多了之後產生的信任。
亞當·斯密(Adam Smith)
既然人不完美,社會就不能靠道德撐住;只能靠制度、分工與規則,讓普通人也能好好過日子。
這就是愛丁堡的底氣:不相信奇蹟,只相信制度。
他們不談神蹟,只談制度、法律與市場。
這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文字遊戲,而是一場浩大的城市實驗:
• 設計出的紀律:筆直、對稱、網格狀的「新城」拔地而起。它像一張乾淨的白紙,強勢地蓋住了舊城混亂、骯髒且充滿詛咒瘟疫的記憶。
• 制度的潔癖:理性不再只是遙遠的詞彙,它被寫進法律、被教進學校,用兩百年的時間,把原本活在恐懼中的人,整流成守時、守法、守分的文明公民。

思想家大衛休謨常去的小酒館 圖/wikimedia
三、沿用的習慣:帝國退場,人們靠秩序渡日
到了20世紀,大環境再次劇變。
兩次世界大戰重創倫敦,大英帝國的版圖快速解體,英國失去了對外施力的肌肉,只能轉向內部尋求共鳴。
這時,愛丁堡這座早已習慣「自我管理」的城市,成了國家最後的心理堡壘。
但理性與紀律如果變成理所當然,就會被遺忘。因此,秩序必須被「儀式化」。
軍樂節的誕生
1950年的戰後歐洲充滿了「混亂感」,軍樂節(Military Tattoo)的精準步伐,對當時的人來說不僅是表演,更是一種「世界還沒垮」的慰藉。
這不是娛樂,而是把兩百年來學會的「自我約束」,濃縮成一場讓你起雞皮疙瘩的表演。

圖©The Royal Edinburgh Military Tattoo
倫敦負責衝刺,愛丁堡負責穩定
很多人以為,愛丁堡的角色只存在於泛黃的歷史裡。但在大不列顛的性格版圖中,它至今仍占據著一個不可或缺的「壓艙石」位置。
在英國人心中,倫敦與愛丁堡從來不是競爭對手,而是分工明確的兩種生命節奏。
• 倫敦:是引擎,代表權力、金融與永不休止的全球速度。它必須快,必須在浪潮尖端與世界搏鬥。
• 愛丁堡:是羅盤,代表制度、歷史,以及一種「可被信任的慢」。
英國人之間流傳著一句極其精準的私房話:
「倫敦決定事情會不會發生,愛丁堡提醒我們事情『該不該』這樣發生?」
這可不是文學修辭,而是冷靜的制度現實。

新城的設計師James Craig 圖/wikimedia
當倫敦的節奏太快、權力過度集中時,愛丁堡的法律、教育與那份根深蒂固的自治傳統,就像是一組精密且優雅的「剎車系統」。它用整座城市的慢,去抗衡那個時代的急。
而這份「被信任」的地位,是愛丁堡在商業洪流中,極其克制才做出的三個長期選擇:
• 拒絕過度娛樂化:她沒有把厚重的歷史,改造成廉價的迪士尼樂園。
• 拒絕完全商業化:即便是熱鬧到極致的藝術節,骨子裡仍堅守著「創作優先」的文人傲骨。
• 拒絕資本的吞噬:她將靈魂保留在「皇家哩路」的獨立巷弄與石板路中,拒絕讓資本市場徹底抹去城市的記憶。
這座城市不急著投入資本主義的懷抱,它更在意的是:當世界越走越快、快到讓人站不穩時,自己還能不能是一塊讓人心定的「黑色岩石」。

市中心的王子街 圖/Shutterstock
理解愛丁堡,其實也在理解我們自己
愛丁堡的秩序,不是天賦,也不是美學。
它是一座城市在多次崩潰邊緣後,做出的集體選擇。
從恐懼到理性;從理性到紀律;從紀律到儀式。
當你站在城堡前,聽見軍樂節那聲劃破夜空的長笛,你目睹的其實是一件極其人性的事:看見人類如何在失控的廢墟上,拍掉身上的灰塵,重新學會把自己站好。
👉 回到策展母文:《愛丁堡,一座不給你成功壓力的城市》
延伸閱讀|愛丁堡七篇策展報導
這不是一份旅遊攻略,
而是一組用城市側寫,寫給不同狀態旅人的文章。
你不需要照順序閱讀,只要從此刻最貼近你的那一篇開始。
B《城市骨氣:愛丁堡如何從恐懼走向秩序》
► 《英國+愛爾蘭深度全覽19日》
如果你想去英國與愛爾蘭,又不想花力氣研究交通、住宿與景點,不妨參考
愛丁堡轉型常見問題
Q1:愛丁堡舊城與新城的風格為什麼差異這麼大?
這反映了愛丁堡的「心理大轉向」。舊城是中世紀「恐懼治理」的產物,擁擠且混亂;新城則是18世紀「蘇格蘭啟蒙運動」後的理性實踐,強調對稱、通透與制度化的美感,象徵城市從迷信走向科學的轉捩點。
Q2:蘇格蘭啟蒙運動對愛丁堡的秩序有何影響?
啟蒙運動讓愛丁堡不再依賴宗教恐嚇來維持社會穩定。思想家如休謨與亞當·斯密提出以法律、市場與自我約束取代舊有的權威治理,這促使愛丁堡建立了極其嚴謹的教育與法律體系,奠定了今日「紀律之城」的根基。
Q3:為什麼愛丁堡軍樂節是一種「文化儀式」?
軍樂節不僅是表演,它在 1950 年誕生之初,承擔了戰後心理重建的重任。它透過軍事化的高效協作與精準節奏,將抽象的「紀律」具象化,讓在戰亂中失去安全感的民眾,能透過視覺與聽覺重新感受到「秩序依然存在」。
Q4:來到愛丁堡旅遊,該如何感受這種「秩序感」?
建議先步行穿越舊城的窄巷(Closes),感受當年的壓抑與混亂,再走向新城的喬治大街(George Street)體會理性的遼闊。最後,在八月參加軍樂節,在鼓聲中親身體驗這座城市如何將生存的掙扎轉化為極致的藝術。
| 本文未經同意,禁止轉載 |